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使得能源投资逐渐转化为制造业投资
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与盈利改善,使得能源行业发生巨变,不再依靠自然资源的天然分布
传统能源行业源头是采矿业,高度依赖资源禀赋。传统能源行业,利用的是煤、石油、天然气、水电等常规能源,其中前三类为化石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能源,高度依赖矿藏分布,其核心是能源矿产的开采。因此,储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的北美与澳大利亚、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俄罗斯、伊朗等国家与地区,在传统能源行业占据绝对的发展优势,一方面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能源支持,另一方面出口能源牟取利益,同时可以对他国施加能源威慑与资源掣肘。
新能源行业本质是制造业,高度依赖制造业技术水平而非自然资源。新能源是在新技术的基础上,以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取代资源有限、对环境有污染的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相较于传统化石能源,新能源的优势在于:(1)可再生性与永续利用;(2)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不依赖矿藏;(3)不含碳,减轻碳排放。因此,发展新能源行业,既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减轻碳排放的环保目的,也是基于降低对国外进口能源依赖的战略考量。相较于传统化石能源,新能源的不足在于:(1)能源密度低,开发利用单位成本高;(2)间断式供应,波动性大,对持续供能不利,更需要及时储能。因此,发展新能源行业,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是一次能源端能源开采的成本问题与效率问题,其次是二次能源端电能的有效储能问题。
由此可见新能源产业发展本质需要依赖制造业技术水平。从节能减排的视角看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会产生至少两次碳排放:一次能源(石油、煤炭)转化为二次能源(汽油、煤气)时会产生一次碳排放;二次能源(汽油、煤气)在燃烧转化为可直接利用的电能时会产生二次碳排放。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1)在开采阶段就能高效率、低成本地将可再生能源等转化为电能;(2)将电能及时储能,以电池取代汽油、柴油、煤气等作为清洁环保的二次能源储能载体。
风电整机、光伏板等研发制造与新能源电池制造这两类技术的突破,就是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关键,中国发展潜力大。前者解决的是清洁能源开采端(一次能源)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电能的高效储存与清洁利用(二次能源)问题。近年来,在政府投资与补贴支持下,我国在风电整机制造、光伏板制造、动力蓄电池制造等领域都有了快速的发展突破:2020年我国新增和累计光伏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风电整机制造技术达国际水平,2020年全国新增风电装机量同比翻倍;新能源动力电池装机量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需求量的增长而逐渐攀升。我国制造业根基与研发基础较强,结合供给端核心技术的突破、产品质量的提升与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下降,及需求端清洁能源需求的高涨,都会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业的持续发展。
传统能源行业与新能源行业,本质上是能源行业与制造业行业之间的差异。传统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消耗与成本攀升,新能源领域的技术突破与盈利改善,都会使得未来的能源行业发生巨变:未来,能源行业的制约条件将不再是能源矿产的储量与分布,而是新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如风电机、光伏板、蓄电池等设备的制造水平。因此,我们看好中国未来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潜力,看好相关制造业的景气度与增长空间。
能源行业过去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巴西、俄罗斯、中东等国是主要优势国家
传统能源行业过去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俄罗斯、巴西、中东等国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国家,具有自然禀赋优势。资源型国家特指对资源依附能力较强的一类国家,世界上具有典型的资源禀赋优势的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巴西与中东等国,其优势也各不相同:俄罗斯资源禀赋主要体现在原油、天然气、钢铁和煤炭。俄罗斯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着世界上最大储量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丰富的能源储备也深刻影响了俄罗斯的国民经济,使其成为重要的能源出口国,2020年俄罗斯主要的出口品有石油和石油产品、铁类金属、天然气、煤炭,占俄罗斯总出口的比例分别为40%、8%、4%和9%,合计高达61%;对于巴西,其资源禀赋优势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和铁矿石,巴西拥有全球第二大的森林、全球三大牧场之一的南美牧场,还拥有全球第五大的耕地,这决定了巴西在农产品种植方面的先天优势,此外铁矿石也是巴西重要的矿产资源,2020年巴西铁矿石产品占全球总产量的16.7%,位居世界第二;对于中东国家,其资源禀赋优势主要体现在原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和伊朗均是传统的产油大国,2020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约占全球石油产量的30%,对石油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能源行业当前主要取决于人口质量红利:中国是主要优势国家
中国在全球具有突出的人口质量红利优势。近年来,我国人口质量红利不断强化,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和科研型人才总量出现较快增长,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已达到1226万人,其中研究生毕业生数和普通高校毕业生数较2004年分别显著增长301%和215%,劳动力的质量不断提升。此外,科技人力资源也保持较快增长,高校研究与发展人员从2004年的24万增长至2018年的44.5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超美国,此后持续稳居世界第一。
能源行业当前取决于人口质量红利,中国不断强化人口红利优势,未来在以高技术为主驱动力的新能源行业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人口质量红利相对人口数量红利,一般是指通过劳动力质量提高对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我国政策着重强调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及劳动力技能,劳动力要素红利着重“质量红利”而非“数量红利”:
其一,在基础教育方面,从十九大报告到十四五规划,加强基础教育一直是教育领域改革的重点关注方向,中国基础教育未来15年的目标是建成教育强国,“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二,在职业教育方面,强调健全技术工人职业发展机制和政策,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其三,在放开大城市落户政策方面,推动落户政策限制逐步放松,落户规模大幅增加,鼓励高技术人才落户当地;其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提高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多项政策齐发力,旨在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国人口质量红利优势,尤其是放开大城市落户条件,推动城市群一体化,有助于高素质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制造业优势充分发挥,2020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披露,我国新能源规模开发利用规模迅速扩张,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截至2019年底,在运在建核电装机容量6593万千瓦,居世界第二,在建核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
发达国家过去先发展后治理既有认识原因也有成本原因
发达国家过去经历了先发展、后治理的过程,呈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即倒U形曲线,最早由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用于反映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将库兹涅茨曲线的应用拓展到环境科学领域,通过对42个国家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环境污染或退化程度(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量)也随着经济发展(人均GDP)而先加重后减轻,污染物的排放量会在达到一个峰值或平台后逐渐降低,长期呈现倒U形,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此后许多学者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作为一条经验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充分展现了发达国家过去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普遍模式。
发达国家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转折点大致出现在20世纪30-50年代,历史上影响重大的污染事件往往成为环保立法的重要转折点。事实上,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发展造成的污染就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如20世纪初,老牌工业国家英国首都伦敦就有“雾都”之名,但其严重危害直至20世纪30年代起才逐步受到大范围关注。例如,著名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30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0年起)、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和日本水俣病(1953-1956年)在造成成百上千人患病或死亡、破坏社会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等严重后果后,都引起了公民和政府对于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议题的广泛关注,进而推动相关环境法订立推行和各项防治污染针对性措施的落地。至20世纪70年代,各发达国家普遍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境治理,经过数十年的污染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也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从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工业生产方式优化和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逐渐走完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
发达国家过去先发展后治理有认识原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发达国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高能耗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等污染物可能造成的危害。过去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环境治理行动、环境法的推出,往往来源于产生较大危害性和社会影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后的民意推动,而非事先认知和防范。例如,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伦敦烟雾事件的成因实际上有相似之处,都是大量车辆尾气或工业废气排放在当地特殊地形、天气条件叠加作用下形成难以扩散的污染气体导致损害生命健康,而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复杂条件叠加导致的结果很难实现在污染危害发生前预见并预防。美国洛杉矶更是在1947年污染事件发生后专门划定空气污染控制区,研究空气污染的性质及其来源。
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也有成本原因。一是工业发展初期和中期,牺牲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代价较高。在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中,直至实现较高人均收入水平的转折点以前,治理污染的处理成本和节能生产成本较高。例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脱硫设备、脱硝设备、污水过滤器等环保设施的工艺研发和生产制造仍处在初级阶段,各项厂商加设环保设施、使用节能新型生产模式的经济成本较高,为节能环保政策的实施落地带来较大阻力。二是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推行包括工业生产方式优化在内的污染防治、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安排的决策成本和制度成本较高。这就导致在一些恶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并引发广泛关注前,发达国家社会整体对于工业生产排放污染物、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容忍度较高。
当前中国可以发展与治理同步的条件基本具备
发展经济与治理环境不必然相斥。即使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也存在争议,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际上是一种经验现象,而非客观规律。我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主要还是由于认识不足和成本较高两方面因素,而如果在认识和成本方面的障碍得以克服,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也能够并行。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基本具备发展与治理同步的条件。在认识层面,我国充分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借鉴经验,在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更严重的恶性环境污染事件之前,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中国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丰富:早在80年代,中国就将保护环境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的环境保护三大政策;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宣言》中,中国首次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计划;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充分凸显污染防治的重要战略地位;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我国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2021年3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在成本层面,制度优越性和环保技术的发展有效降低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制度成本和经济成本。一方面,中国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举全国之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防治环境污染和抑制高耗能产业,加速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脱硫、脱硝和污水处理等节能环保设备的工艺与生产已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当前对于我国工业企业而言,增设环保设施和改用节能生产模式的经济成本相比发达国家“先污染”时期已有显著下降。
事实上,从新能源领域视角来看:碳中和时期发展新能源本质上既是治理,也是发展,新能源领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考验与锤炼的是大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及人力资本积累,由此可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带动新一轮经济发展。我国当前具备将发展与治理同步的条件,在发展层面兼具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与人口质量红利,坚定看好碳中和可能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空间。
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也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目前全球范围来看,绿色发展相关技术仍有竞争空间,如氢能、储能、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及涉及到清洁能源技术的新材料、芯片制造等领域均是全球竞争的焦点。当前中国在光伏、风电、储能等多方面处于领先,但在半导体等基础技术方面仍然相对落后,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基础研究强度长期落后于国际发达国家,美欧韩日等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均是我国的2-4倍,研发强度、基础研究强度双双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亟待改变。目前我国相关政策已经有所侧重,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十四五期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为6.2%,十四五期间计划提升幅度为1.8%,高于十三五期间约1.1%的提升幅度,说明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我们认为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我国基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实现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从这个维度看,当前相关传统、落后产能向境外迁移的问题对于国内整体制造业投资而言问题不大,未来经济发展更重“质”而非“量”,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将推动国内整体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
风险提示
新能源技术进步与盈利改善迟缓;政策不及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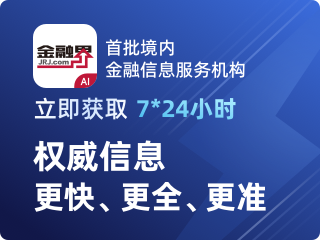
- 银行股迎来“黄金买点”?摩根大通预计下半年潜在涨幅高达15%,股息率4.3%成“香饽饽”
- 华润电力光伏组件开标均价提升,产业链涨价传导顺利景气度望修复
- 我国卫星互联网组网速度加快,发射间隔从早期1-2个月显著缩短至近期的3-5天
- 光伏胶膜部分企业上调报价,成本增加叠加供需改善涨价空间望打开
- 广东研究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助力商业航天快速发展
- 折叠屏手机正逐步从高端市场向主流消费群体渗透
- 创历史季度新高!二季度全球DRAM市场规模环比增长20%
- 重磅!上海加速推进AI+机器人应用,全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盛大开幕,机器人板块持续爆发!
- 重磅利好!个人养老金新增三大领取条件,开启多元化养老新时代,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喜人!
- 重磅突破!我国卫星互联网组网速度创新高,广东打造太空旅游等多领域应用场景,商业航天迎来黄金发展期!





